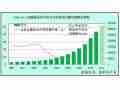前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遇到了最大的挑战—能源不足。石油、铁矿石、天然气以及一些稀有金属均需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尽管煤炭资源丰富,但在环保为先的世界大浪潮中,如何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国际经济地位与政治、文化地位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如何参与国际能源定价?
王湘穗:能源定价机制可以说是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环节,是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经过大国博弈和多次战争形成的。从工业时代初期开始,围绕能源产地控制和能源定价权的争夺就没有停止过,某种意义上这甚至是20世纪历史的主线。现在的能源定价机制是这个历史的结果,其背后是国家实力。这就有点像一个股份公司分红,谁来分配、谁分到多少,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凭实力说话的。要想改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现在中国有意愿参与国际能源定价,这是对现实国家利益的关切。但必须认识到这套机制背后的历史渊源、力量结构。国际能源定价机制决不是出价、议价这么简单,不是光靠谈判就能改变的。需要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当中长期博弈之后才有机会。
李晓宁:所谓“国际能源定价机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历史上西方国家最初搞石油工业的时候,有两种能力非常重要:开采能力、对产地和运输线的军事控制能力。两次大战时石油产地和运输线都是军事角逐的重要目标。二战后进入和平时期才从控制开采技术和产地发展到控制交易环节,也就是交易所。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海湾国家为了与西方对抗搞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之后,有了讨价还价的双方,才有了“能源定价机制”。20世纪70年代初的金融危机使得石油与美元挂钩,此后石油成了金融市场的风向标。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激增是成为制造业大国之后的事情,与当初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产地和运输线不能像当年西方那样去占领了,石油只能在西方的交易所里去买。但现在的世界也不是靠军队就能控制石油的时代了,参与从石油勘探开发到交易的各个环节,学会在各种交易节点当中占优,在博弈不是用枪的情况下如何占优,才是参与定价机制的方式。
如何保障中国能源战略航道的安全?
王湘穗:中国的经济重心在沿海,这是导致能源来源严重依赖海路的重要原因。这种经济布局是存在问题的。所以首先要解决的其实是能源对海路的依赖的问题,而不是对战略航道的控制权争夺问题。其次,应该开辟多元化的能源通道,注重陆上能源运输线的建设。中亚、中俄、中缅天然气管道都会降低我国对于马六甲海峡的依赖。此外,巴基斯坦是潜在的可以直接连通中国和波斯湾的通道。
李晓宁:石油安全不是你控制了油井和航道就安全了,而是要在日常的交易中能够迅速拿到你所需要的石油量。要说控制产地,现在美国都无法通过军事方式控制伊拉克,美国是以“推翻暴政”的名义进去的,那法理上完成这个使命之后你就得撤出。要说控制运输线,现在海盗都能对油轮构成威胁,恐怖分子都能轻易破坏输油管道。21世纪更多的安全问题不是国家制造的,而是恐怖分子制造的。在石油的阀门不是由军队来操纵,而是由金融家来操纵的时代,最大的能源安全问题不是来自军事方面,而是来自价格的剧烈波动。最主要的工业原材料价格可以在短时间内从147美元到36美元大幅震荡,这是工业体系所不能承受的。我们需要新的能源安全观。
如何协调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纷争?
李晓宁:要跟供应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就不能只对人家的资源感兴趣,也得给人家东西。能够长期共生的东西一定是互惠的。这就需要设计新的融合机制,而不是靠过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关系形式。
王湘穗:“走出去”战略是必须坚持的。我们在“走出去”过程中受到各种阻碍说明人家对我们有防范心理,这里有国际政治原因,也跟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程度不够有关,海外并购涉及各国不同的法律程序、社会关系、经济结构以及历史文化诸多层面,不是学习书本这么简单。我们还有一个心理是老想着控股,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只是参股而不是追求控股,可以大大减少并购过程中的阻力,同时能够达到保障自己权益的效果。
如何平衡煤炭与清洁能源的关系?
李晓宁: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高是跟工业结构有关系的。中国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本身就是把工业体系中高能耗、高污染的部分给承接过来了,以极其低廉的价格造出如此大量的工业品是没有办法不去选择成本最低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对于高能耗工业体系不能一直依赖下去,但也不是靠改变能源种类就能改变这种状态的。采用昂贵的新能源不仅仅是成本问题,还有工业体系的适配问题。高能效、低排放的清洁煤炭技术比改变能源构成更具有现实性。
王湘穗: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该对其历史累计排放量承担责任。而这种责任也应该包括尊重一国的能源资源禀赋。中国的能源禀赋基础就是这个样子,违背这个基础的路线是不现实的。另外,发达国家的责任也应该包括清洁能源技术转让。如果“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真的是为了人类的命运,那发达国家就不应该在清洁能源技术上索要高价,应该担负起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责任。(来源:时代周报)